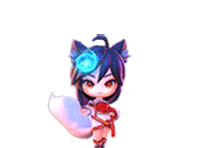|
|
我一直在回避我的身世,就像我在单位,回避着我写诗这样的事实。我不肯承认我写诗,不想叫单位的同事或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我偷偷地写,正因为偷偷地写,所以写诗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偶有灵感,在办公室总是写一行就习惯性地蒙上一行,这行为,变得秘密,这日子,变得有意思起来。
刚来陕西的时候,我一说到我是湖北的,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武汉,继而说:“武汉好地方啊,咋就来咱这儿呢。”武汉是好,可武汉不等于湖北呀,在湖北的地图上,有很多不被标示出来的村庄,我就躲在那样的村庄里,过了二十多年。感冒,咳嗽,多愁,善感,二十多年。直至后来出走。
在我的第一首诗赤脚奔走的女子中我这样写我的身世:
“在地图不经过的地方
我从春天的腹部萌芽
我没有第一声哭泣
我是一粒干涸的种子”
我肯定是睁着灰色的眼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这双灰色的眼睛,日后,使我看见了世界受苦的事物或事情,就悲哀地想哭。
我在童年失去了优越,在青年失去了爱情,在中年失去了身体(健康的体质),我不平衡。我无法获得幸福感。
感谢这双灰色的眼睛,帮助我找到了对抗与斗争的另一种方式,那些施与我幸福或痛苦的友者或对手,都在诗歌里得到了赞美或宽恕。
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打开自己,我把我的身世隐藏在很多条线索背后。
像一场无法言说的失恋,我的身世是一个包袱,打开是支离破碎的玻璃片,这些玻璃片,互相摩擦,它们其实就是被生活打破的一个个伤口。
只有正视了这一个个伤口,我才能真诚地不在诗歌里掺假。否则,我像悬浮在空中的物质,没有故乡,没有情感的落脚点。没有故乡的人,是没有诗歌的!
三个年头了,我在诗歌里坚强起来。心中的病渐渐痊愈。我想大声地说:我是穷人的女儿,我有一个高贵的村庄。
我的村庄,在湖北,离武汉有四百多里的一个小县城,离小县城有一百多里的一个小乡镇,离小镇有二十多年的一个小村子。用脚步来丈量,偏僻遥远,用诗歌来丈量,可亲可近。
每隔几年,我就会带上积攒的一笔钱,谨谨慎慎地穿过中原大地,去探望我的村庄。坐了火车转汽车,强烈晕车,甚至呕吐,但我在路途上是不敢睡觉的,我护着一笔血汗钱啊。这笔血汗钱,见证了我在外的辛苦岁月,凝聚了我的劳作,智慧,还有孤独。
当然,我的年过七旬的老父亲,至今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的老父亲,他也许看不见这隐形的一切。
只要父亲微笑,我就会努力地把这奔波的日子进行到底。
疲累,艰辛,偶尔的小幸福,一瞬间的风花雪月,于我来说,这就是诗歌。
我写我的忧伤岁月,写我的多雾的青春,写无数个点,写无数个面,写穷人的脚印,写悲美的丢失……
“我喜欢用符号来记载象形的岁月
看东山的月亮
一轮又一轮流失成弯弯的小河”
今天的星星和明天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假如今天幸福,我把今天的星星叫温情;假如明天痛苦,我把明天的星星叫忧伤——诗歌使万物在新的角度上欣欣向荣。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




 窥视卡
窥视卡 雷达卡
雷达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16-10-21 20:30
发表于 2016-10-21 20:30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