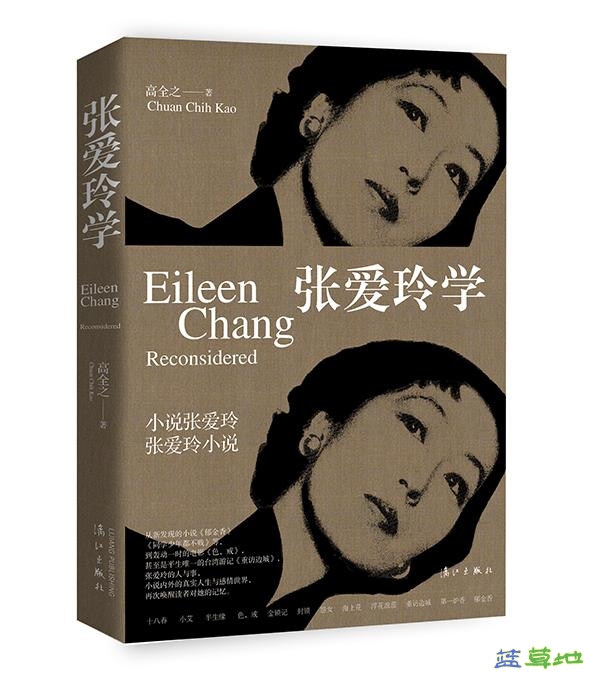张爱玲学:她并非反共作家 也没有为汉奸翻案
[摘要]我们无法考证张爱玲写《秧歌》时候是否拥有这些历史知识,但是从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译写过程里,她确实曾经决定放弃质疑,改为尊重以中国为本位的战略思考方式。 【原编者按】时至今日,张爱玲早已成为一门学问,而要论张爱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台湾作家高全之的《张爱玲学》不得不提。最近,《张爱玲学》的大陆版终于出版了。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论张爱玲政治观的部分。
《张爱玲学》,高全之/著,漓江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1 评家早已注意到张爱玲未曾否定共产党。在小说文本以外,以旁证支持这种看法,司马新访谈张爱玲继女霏丝女士(赖雅首任妻子的女儿)的记录,最值得一提: ……霏丝女士道,在六十年代初,她曾问张爱玲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有何看法,张爱玲并未作直接回答,而是说:“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一个社会比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还要坏。”这当然并非表示她拥护共产主义,但证明她对新中国看法很是复杂,并不仅是“反共”而已。到今天还有少数文评人,称她为“反共作家”,好像她专门写政治小说,不足观矣。 在小说文本之内求证,自然更具说服力。我们在《大我与小我——〈十八春〉、〈半生缘〉的比对与定位》曾指出《十八春》描绘了国家大我振奋与提升个人小我,而对当时的中国新政权做了肯定。我们在《〈小艾〉的无产阶级文学实验》曾引陈子善的意见,说它可能是作者对新中国短暂的、善意的肯定。本文第四节提到张爱玲以人类通性作为共产党员革命经验合理化的依归;尝试了解共产党员,也是不全面否定共产党的一种证明。我们可以在被标签为政治小说的《秧歌》里另举三个例子,说明张爱玲的态度颇为复杂。 其一,作者从未质疑土改的原始目的——重新分配农地以及财富。《小艾》提到贫农金福满怀希望返乡,因为土改会分他田地。《秧歌》描写土改时候把地主的家具与日用器具硬性分给农民。金根分到红木雕花大镜。平常胆怯的金有嫂一提起那面镜子,竟兴奋过度与婆婆谭大娘抢着发言,次日与月香私谈还念念不忘尽夸不止。她的过度反应显然暗示了土改前农村贫富悬殊。月香返乡当晚,金根从箱底取出地契,两人仔细研究,金根说: 这田是我们自己的田了,眼前的日子过得苦些,那是因为打战,等战打完了就好了。苦是一时的事,田是总在那儿的。 月香当时“非常快乐”,对“幸福的未来”觉得有“无限的耐心”。可见作者反对土改的激烈方式,可是肯定了农地与财富重新分配的需要。 其二,作者并不忽视当时中国抗美援朝的官方的说辞。《秧歌》借由干部发动农民做军鞋的一段话,反映当时中国担心美军借道朝鲜半岛打入中国大陆: ……我们的战士穿着这鞋要走上几千里地,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要不是亏了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挡住了他们,美帝早打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们无法考证张爱玲写《秧歌》时候是否拥有这些历史知识,但是从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译写过程里,她确实曾经决定放弃质疑,改为尊重以中国为本位的战略思考方式。 《秧歌》没有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证明,是新四军的军纪。《秧歌》写王霖、沙明凭着一腔报国热忱参加新四军,作者原本就毫无讥讽之意。王霖的部队半夜奉命撤离乡村,共产党士兵彻底执行“不取民间一针一线”的口号,即刻挨家挨户归还借用的物件。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向村妇致谢时说: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这种军敬民的美德令人称羡,足以收录于任何国家部队训练操典里,视为行为准则。只知鞭打共产党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如此的情节。 2 张爱玲小说涉及汉奸问题,始于《十八春》。由于她借此课题批判国民党,所有汉奸笔墨在改写为《半生缘》过程里全部删除。两起汉奸情节都质疑汉奸的基本定义,以及政府处理汉奸事件过度严苛。第十五章提到顾太太在六安城的经验: ……日本兵进城的时候,照例有一番奸淫掳掠,幸而她小叔顾希尧家里只有老夫妇两个,而且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并没有受多大损失。但是在第三天上,日本人指定了地方上十个绅士出来维持治安,顾希尧因为从前在教育局做过一任科员,名单内也有他。其余都是些有名望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这些人本来没有什么国家思想,但是有钱的人大都怕事,谁愿意出面替日本人做事,日本人万一走了,他们在这地方却是根深蒂固,跑不了的。当然在刺刀尖下,也是没有办法。不想这维持会成立了没有两天,国民党军队倒又反攻过来了,小城的居民再度经历到围城中的恐怖。六安一共只沦陷了十天,就又收复了。国民党军队一进城,就把那十个绅士都枪毙了。 显然作者同情被迫担任伪官,惨遭枪毙的那些乡绅。十六、十七两章两度提到慕瑾蒙冤为汉奸被捕,太太受拷打惨死。此情节再度强调汉奸罪名滥施。作者不平则鸣,也有史实根据。南方朔说得好:“用忠奸之辨来禁锢他人或惩罚他人,是一种历史上的过度残酷。读国民党历史,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蓝衣社’和各种特殊行刑队在沦陷区的诛杀‘汉奸’,甚至许多民间商界人士也都无法幸免。派人暗杀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人,或许合乎战争规则,但连只不过为了身家性命或虚荣的商人也被当成汉奸,未免太过不仁。” 《十八春》之后,《小艾》服膺外在的文学教条,简单化问题以免犯政治错误,就只敢刻意矮化汉奸。 张爱玲离开大陆以后的小说《色,戒》(一九七八)重访这个课题,就尝试从汉奸易先生的立场去合理化他自己的行径。这种小说方法引起误解与臆测,作者特别写《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及在《惘然记》(《惘然记》自序)与《续集》自序数度澄清。揣摩反面人物的内心,描绘他自以为是的思维与情绪,就是在政治信念之外——不论作者是否认可这些政治信念——留意到人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惘然记》这段话: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弥撒”还有它的魅力。 沿用“敌人”、“鄙夷”的字眼来描述汉奸,可见作者不图为汉奸翻案洗清罪名。然而她确实肯定了由了解而导致原谅的可能性。她从反面人物的立场观照世事,或是提到反面人物的人性弱点,都清楚知道设身处地或软心肠可以通达饶恕与同情的大道。她不介意允许那项转折的萌机。这是张爱玲小说涉及政治而能超越政治的诸多原因之一。 对习于汉贼不两立思维习惯的读者而言,这种心存慈悲的姿态自是大逆不道。身临沙场的士兵必须具有高昂的敌我对立的士气,不然如何打胜仗?亲受八年抗战摧残的中国人往往一生无法宽恕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熟悉历史掌故的游客,面对岳飞坟前跪立的秦桧夫妇雕像,仍然吐口水、打耳光。张爱玲没有说这些昂奋的敌意是错的。二元论的敌我意识形态在个人、群体以及国家的竞争或战争里,往往是必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未来的人类战争里仍然会有降臣降将。那种必要的战斗意识无法波及每一个人,因为人性里有那普遍存在的软弱与贪生。 我们不必把这种情愫完全归因于她和(亲日汉奸)胡兰成的特殊婚姻关系。当然那份情缘并非毫无关联。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直接间接耳闻目睹的汉奸,当不止胡兰成一人。比如说,周作人与她同时期在上海《亦报》发表文章。在《小艾》出土的年代(一九八七),大陆学者就曾为周作人在日伪政权任职之旧事而重新评估讨论。所以张爱玲的汉奸关切必然是超越私人情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