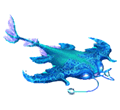|
我在异乡小城定居已三十余载。每逢春节,漫步街头,华灯璀璨如星河倾泻,商场里循环播放着喜庆乐章,手机屏幕上红包如雨纷飞。可这一切精致的热闹,却像隔着一层玻璃,始终暖不透心底。 高墙内的春节演出年年办得隆重。那些身陷囹圄的游子,将乡愁碾碎了融进歌声里。聚光灯下的笑脸越是灿烂,越是映现铁窗投下的阴影。而某些装点华丽的拜年场面,那些精心包装的礼盒在手中传递时,我总会感受到有别的什么在空气里无声流转——那是比礼品更沉重的利益权衡。 城市的春节像被抽去灵魂的华服,亿万灯火织就的盛景下,邻里相遇时仓促的点头,电梯里敷衍的一句“新年快乐”,都成了现代年味的注脚。偶有零落鞭炮声划破寂静,反倒像在提醒这盛大之中的清冷。 可这声响总会把我拽回童年的老家——一个湘北山村。那时的年味,是窖藏在岁月深处的陈酿。 最先嗅到的年味,是在李裁缝的脚踏缝纫机哒哒响起时。新布的清氛混着老太太们絮语,在冬阳里织成暖雾。外婆彻夜守着的麦芽糖锅咕嘟作响,甜蜜缠绕着外公炸麻花的油香,从这家灶台又飘往那家窗棂。 杀年猪那日,年味达到第一个高潮。精壮汉子们奋力降服挣扎的肥猪,雪亮尖刀抽出时,滚烫的血气混着稻草香冲天而起。这并非残酷,而是土地子民对丰收最直白的祭奠。 大舅舅的舞狮队在前厢房吵得沸反盈天。为狮头该缀红缨还是黄穗,为谁扛狮尾更能踏准鼓点,他们吵得面红耳赤。可这争执里漾着热气腾腾的认真——那时的人,连争执都透着肝胆相照的坦荡。 真正的狂欢在除夕夜迸发。爆竹把夜空炸成白昼,狮影在硝烟中翻腾。外婆朝着我兜里塞满花生红枣,粗糙的手抚过我稚嫩的脸颊:“乖孙又长了一岁。”她的笑容里,藏着千年农耕文明对时间轮回的虔诚。 如今返乡,高速公路直通村口,青瓦平房多数变成了小楼。可新建的文化广场却空无一人,几盏太阳能路灯孤零零地亮着,照见水泥地上未拆完的塑料膜。老屋院坝里,荒草已没膝。 稀疏的爆竹声里,我忽然明白:年味从来不只是仪式,而是那群愿意为仪式倾注热忱的人。当年外公炸麻花的锅台已经蒙尘,当年舞狮队的争吵消散在风里,当再也无人愿花整夜熬制一锅麦芽糖——年味的魂,便随之而去了。 我们在财富的阶梯上步步攀登,却把某些珍贵的东西丢失在来路上。物质丰盈了,可那些需要时间慢酿、用真心发酵的情谊,却在新世界的缝隙里悄然蒸发。故乡仍在,只是那个用体温互相取暖的村庄,已幻化成了折叠在时光深处的剪影。 站在老屋门槛望出去,新贴的春联墨迹未干。几个孩童低头刷着短视频,指尖划过别人编排的热闹。 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盛,却让灵魂在看不见的地方流离失所。这或许就是变迁的代价——每个人都在回家,但那个能让灵魂安住的年,我们却在怅然若失地四处寻找。
| 


 雷达卡
雷达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25-10-1 10:05
发表于 2025-10-1 10:05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