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初冬的朝霞给黄石北站镀上一层玫瑰金,动车组银白色车体切割开站台上凝结的霜气。六公里外的普速车站仍在晨曦中沉睡,而这里已然人声鼎沸——现代人出行的轨迹,终究是要沿着高铁的银色琴弦滑向更便捷的远方。顶棚冰凌垂坠成水晶帘幕,北风掠过时,竟真发出“呼…呼呼呼…”风铃的清脆声响。
五号餐车暖暖的,车窗上沾满了雾水,呵一气都能作画。忽然瞥见两位戴着绛红色羊绒围巾的老者。她们都是以前在黄石火车站工作的退休职工。此刻貂绒大衣掩不住臃肿的身躯,倒是腮红抹得比当年上班时还要鲜艳些。
"老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非典的时候?""怎么不记得,都戴着口罩生怕自己中标了,也没有想到新冠更厉害..."声浪在密闭车厢里格外嘹亮,像两只不知疲倦的知更鸟说个不停。
鄂州站的电子钟跳成09:10,新上车的灰发妇人扶着椅背张望。米色羽绒服起了皱褶显得陈旧。"冬梅!"其中一位突然起身,声调像踩下急刹车的铁轨般尖锐。被唤者转身的瞬间,围巾滑落露出后颈的老年斑,却浑然不觉地绽放出少女式的惊喜笑容。
三个老友的寒暄如同失速的列车,在"儿子学区房""儿媳月子中心"这些站台间来回穿梭。当冬梅抱着外甥的奥特曼书包踉跄走向二等座时,貂绒女士忽然压低嗓音:"她当年可是咱们客运段普通话说得最好的播音员,怎么这样老?难道过得不好..."另一位喝着温热的茶水说道:"听说她与她儿媳处不来不住武汉,又回鄂州住了。"
外面的太阳光斜斜切过她们精心卷烫的银发,这时,一位脚步敏捷轻快的年轻乘务员过来查票,她们用像枯枝树皮一样的双手拿出了就医乘车证,动作略显迟钝,与年轻的乘务员娇嫩雪白的双手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三个老妇人在我眼中奇妙地重叠——她们都是被时代列车甩下的旧零部件,却又固执地给自己镀上新漆,就像那呼哧呼哧的蒸汽机一样,早已被飞驰的动车组取代。
|
|




 雷达卡
雷达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25-3-31 21:46
发表于 2025-3-31 21:46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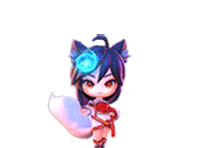

 作者
发表于 2025-4-1 18:03
作者
发表于 2025-4-1 1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