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是我工作的单位,20多年就在这路上来来往往的反反复复中,不觉已是人到中年。某日,在绿荫遮蔽的场区公路上,我偶逢祝大队长。当时他正用力蹬着单车赶路。我招呼了一声:“祝叔,在忙什么呀?”他冲我一笑,说砖厂在扩建围墙,他们请我去监工。
已经是六十多的人了,身手还是那么矫健。除了脸上像路边白杨树皮一样刀刻似的皱纹,还看不出颓废的迹象。我想起20多年前他肩上斜挎一只绿色水壶,脚穿 黄色胶鞋,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巡查工地的样子。真让人感叹“岁月虽失,青山不老”。
在洞庭湖西北涔,澹两水环绕的这片土地上,还生活着许多和他一样的退休警察。几十年里,仿佛身旁的这些白杨树一样,他们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历经了风雨沧桑的洗涤。
1983年,我有事情来到涔旦农场,曾经目睹过这里水灾后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空旷的大地上,灰茫茫一片,几处零落阴晦的砖房,凋敝的树木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垸瘠堤瘦,水患不绝,沼泽决荡,芦苇萧瑟”——这就是早年农场的景观。
鬓发衰白的于科长用他改不掉的汉寿话向我描述:“那个时几,是一片荒芜,芦苇如墙。任务,修堤。部队战士,担心犯人跑;公安干部,又怕任务重,犯人不稳。”他还说,我们搭建芦苇棚子几十栋,有监舍,伙房,工棚。。,每一到雨天,棚子漏水,床湿,被子上盖雨衣,撑伞。。
场志记载:创建者们以芦苇,稻草,楠竹,糊上稀泥,搭建了农场的第一栋监舍和营房,开始了创业的艰难之路。
溃垸,内渍,寒潮大风。。。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农场干警就像白杨树一样坚韧。
我时常翻阅着自己参加编写的这本《涔旦农场志》:
1956年,洪峰迭起,牛路口堤段裂缝三寸,下挫 1.5寸,有干部8人,犯人415名,打桩,填麻袋,三日两晚不得稍停。
1957年,抢救龙家湾漏眼,郭天堡中队干部犯人三天三晚不眠。
1966年,合同铺堤段裂坼1寸,很快撕裂,内坡下沉,杨国之,杨运甫,宋光春等干警带1000多犯人打桩,围堤,堵草袋,填土。。。
1969年,合同铺堤段吊水两公分,全堤溃漫,两处崩塌。。。。。。
1991年,普降暴雨,全场七处堤段漫水,干职工和犯人全部出动抢修14天。。。。。
一双双熬得血红的眼睛,污浊斑驳的衣裤,趔趄疲乏的脚步,泥泞中蠕动的身影。。,这些形象常常透过白纸黑字浮现出来。
现在的农场,已经是一片风平浪静的绿色海洋。纵横交织的白杨树是一抹赏心悦目的景致。饱受车马喧嚣之苦的人们可以在此获得心情的暂时放松和宁静安详。可是面对浓荫的白杨,对这块土地饱含深情的涔旦人心里哪能够平静得下来?在这些两鬓落霜的人心里,或许会联想起曾经历的艰难岁月,已经失去的青春年华,曾经燃烧过的激情。。。
在我的眼里,它们像是熟悉而亲密的老朋友。在曾经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带着一队犯人穿过层层叠叠的白杨树,然后在树下面安排犯人劳动生产。在这些单调枯燥的日子里,我一次次看着树枝上爬满浅绿色的嫩苞,又渐渐挂满浓密的树叶。在微凉的秋风中,那些叶子又慢慢变黄,“嗖”——“嗖”——地时不时飘落下来。枝杈间开始稀疏零落,最后剩下光光的枝干,仿佛老人枯瘦的手掌伸向天空。
我一次次抚摸它灰白的树干,任疙疙瘩瘩的裂纹在手掌中滑动,在它一阵阵的竦动中领受它的友爱深情的致意和问候。
有的时候,我还会以它的枝干搭建临时工棚暂避或者用它的枝叶烧火取暖。我无数次聆听它的吟唱,观看它的舞姿,从来也不曾厌倦过,它总是能牵动我无尽的情思和衷肠。
这坚守和沉默的树,伴随着你我他——每一个农场人一路走过那些难忘的岁月,时时让我们想起某一些熟悉而亲切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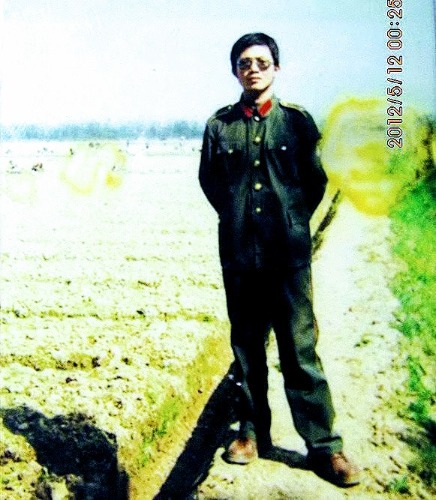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25-5-12 19:20
发表于 2025-5-12 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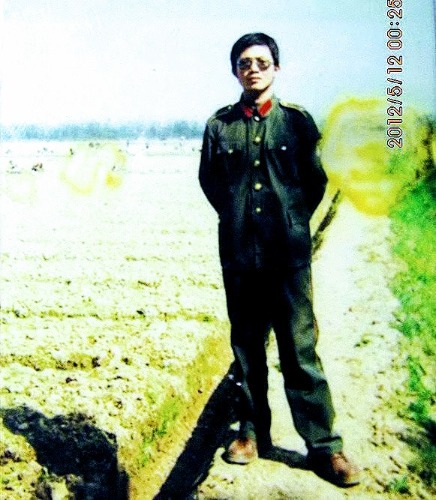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25-5-13 08:09
发表于 2025-5-13 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