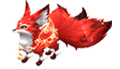|
|
几十年来,农场不断改变着它的面孔。旧面孔纷纷隐去,新面孔不断呈现。曾经与世隔绝、枯乏单调的农场,日渐焕发出新的生命与力量来。
几十年来,我一直审视、打量它,关注它每一丝细微的变化。从前尘土飞扬的场区公路,已经被宽阔平展的柏油路取代。那些低矮逼仄的红砖旧瓦房,被高大巍峨、气势磅礴的巨楼大厦所替换。走出高墙深苑外的农场,纵使日月流失,不仅没有苍老、憔悴、衰败,反而出脱得更加俊美、鲜亮。又糙又黑的老面孔,蜕变得风姿绰约、玉树临风的新容颜。
曾经长满农场田野、路边,绿色海浪般质朴无华的白杨树,不知不觉间消失了,新栽培的樟树、桂树、凤尾松、广玉兰、紫薇、茶花、月季…将整座农场装点得花团锦簇、美轮美奂。
姹紫嫣红、小桥流水的花园,彩色斑斓的健身广场,正重新阐释农场的新的价值理念。街角路边一排排雕塑,又小心翼翼将失去岁月凝固保存下来。农场大步向前的路途上,也会偶尔停下来回首一瞥已经模糊难辨的历史踪影。
真实的历史早已隐没于晦暗的浓雾深处,被厚厚的尘埃掩盖住。
据农场老辈人回忆,农场最初的样子是一望无际的白,洁白无瑕的白。白茫茫的一片连接到天边的云彩。 ——“芦苇似墙,白絮飘飞”。
我没见过“芦花冉冉弄斜晖,十月江天似雪飞”的秋景,就像今天这些新面孔也没见过当年“垂杨低映木兰舟,半篙春水夕阳愁”的春色。可我喜欢追寻那些消失不见的风景和被云烟裹卷的谜团。我心头时不时会长出一丛芦苇,在时光的风中颤动。当夕阳残照、芦苇飘絮,情思会不知不觉被带向悠悠远方。
三十余年前,我偶尔在农场一处浅塘边,见到一丛芦苇风中摇晃,就如历史的帷幕忽然敞开一丝裂缝,裂缝中我一窥当年景象。千万根芦苇正在攒动,鬓发斑白的容颜,加深了秋天的辽阔。
不知从何时起,蒹葭苍苍的景象,又幻化为无边绿色的海洋。纵横交织的白杨,描绘农场另一番模样。掩映在绿潮中的红砖小楼,烘染出农场别具一格的情调。
就像是配合着这变换的节奏,农场干部的服装,早先也是那种白色的,象征纯洁和赤诚,又和无边无际的芦苇融为一体。后来换成了橄榄绿,像白杨树无处不在的身影。穿一身橄榄绿的农场黑脸大叔,从泥土中拔起双腿,推着带竹篓的单车,行走在繁华大街上,成为最惹目亮眼的一道风景。
每次到了夏天,炽热的阳光底下,一个老太太总会拿出去世多年丈夫的白色警服晾晒。她一遍遍抚摸着晾衣绳上挂的衣服,一遍遍喃喃自语,就象和丈夫的亡灵对话。
真实的历史早已藏身于帷幕之后,我们只能从裂缝中偶尔窥探,但无法知悉全貌。我们一边为日新月异的新面孔而羡叹,却又时不时回望正在消失的日渐模糊的旧面孔。但过去只剩下遗迹,只能从偶尔露出的裂缝中窥看,真实已经无从还原。
列维纳斯说了,过去是断裂的,忘掉的。但又会偶尔扰动你。随着时移世易,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苍白莫辩。
芦苇消失了,白杨树也消失了,农场最初的拓荒者一个个凋零殆尽。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骑着单车来到了农场,从此融进这片绿色风景中。这里的冬天,万木萧索,寒风刺骨。炎夏时又酷热难当,旷野在滚滚热浪中一味无言的沉默。春秋两季,又总是大雨滂沱、泥泞难行。就是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锻造出了农场人骨子里一股不辞万难的韧劲。



|
|



 雷达卡
雷达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25-5-13 10:22
发表于 2025-5-13 10:22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