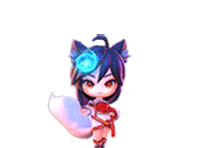|
|
前几天在候车室值勤,刚进门就撞见个眼熟的人,愣了一下便记起了他。立秋已过,天气却仍燥热得很,偶尔几场雨也压不住暑气——这人干脆打着赤膊,许是来蹭空调乘凉的。
他约莫六十岁,矮壮身材,往那儿一站,活脱脱是现实版的“武大郎”。谁真见过书中的武大郎?千百年来不过是揣测,可他这模样,倒让那虚构的形象有了落地的实感。不过他可比武大郎硬气,是家里能拿主意的主心骨。我见过他妻子,个头与他相仿,是旁人眼里“门当户对”的般配;也见过几次他女儿,偶尔来帮着看摊,瞧着个子不高,却和所有孩子一样,是父母眼里最可爱的宝贝。
我记着他,并非有什么交情,甚至从没私下说过话。他是黄石火车站附近的村民,当年征地后,这一带人大多不种庄稼了:年轻人多去城里打工经商,只剩些没手艺、或守着店面的人,在广场上谋生活——这大抵就是城乡交接地带的常态。
第一次留意他,还是十年前。那时广场还没完全建好,左手边一排门面生意火得很,客流不断,他也在这儿守着个铺子,我偶尔去他那里买烟。后来广场整体落成,右手边建了停车场和新门面,出站口也挪到了那边,生意一下全往右手边去了。左手边没了旅客进出,门面一个个冷清下来,没过几个月就全关了门。
干惯农活的中老年人,哪有什么手艺?有本事的早出去找活了,他好不容易守着个门面尝了三年甜头,如今没了收入,哪坐得住?于是他盯上了出站口——在石墩靠绿化带的地方摆起了地摊。广场左右分属两个湾子,右手边的门面地界他沾不上,只能守着这处。
那排石墩是条分界线:外面归广场管理处,里面归车站管。大概是管理处赶过他几次,不让他在里面摆——怕挡了出租车和私家车的道,他便挪到了石墩外。我值勤时见了,总会让他再往外挪挪:出站口本就人多,遇上几百人的车次,一个地摊就能造成拥堵。他倒知趣,每次说他几句,他立马就把装着零食饮料的推车往外推,我也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旅客通行就好。
有回我图近,在他那儿买烟和水,一问价才知比街上贵不少。后来留意观察,发现他的生意是真的好,夸张点说,几乎时时刻刻有人来买。哪个见了不眼热?附近门面的人不甘心也往出站口凑,石墩处一下摆了好几辆小推车,把路堵得够呛。我们车站只管石墩里头,外头的事管不着;可广场管理处急了——旅客一多,私家车、出租车堵得动弹不得,管停车场的师傅不是附近湾子的人,好言相劝不管用,也不敢说重话怕得罪他,只能往上汇报。
上面来了几波人,还是赶不走。我曾听他犟着嘴说:“地被征了,没田种了靠啥活?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摆摊咋行?”话里满是不服软。后来投诉多了——旅客嫌堵,司机嫌乱,管理处没法子,找了街道办事处,又联合村干部一起找他谈。他也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况自己本就是无证经营,最终松了口,同意去附近工业区的铝厂上班。
这一带的居民,就没见过闲着的——除非真动不了了,否则绝不会歇着。你瞧那一排排民居,比城里不少房子还阔气,他们也清楚,这儿的购物、教育、娱乐比不上城里,却依旧知足。闲不住是刻在骨子里的勤劳,不认命、不服输、不服老,是藏在脾性里的劲。就像当初左手边的门面,谁能想到前一刻还红火,广场一建好就垮了?可他们偏不信邪,总要想法子找事做——多干一点,就多份报酬,多份安心,多份踏实的幸福。这不正是中国千万中老年农民的缩影?不也是建设祖国的一支力量吗?
只是这些年见着、听着的事里,总有些惋惜:不少六十来岁的农村人,说生病就走了,很多病本不是绝症,却因为没体检意识、舍不得花钱,硬生生拖成了大事。如今中国社会老龄化越来越明显,这事该被重视——关心他们,既是保住生产力,更是最基本的人性关怀。
|
|




 雷达卡
雷达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25-9-16 17:10
发表于 2025-9-16 17:10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